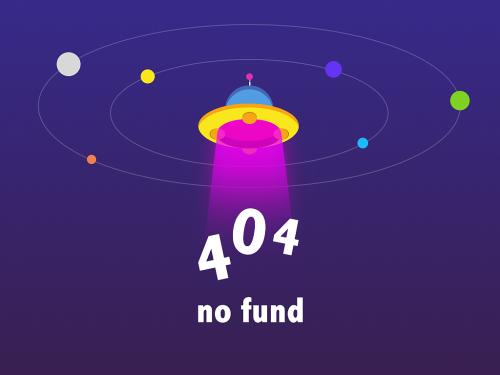 当前位置 : www.凯时首页 》新闻咨询讯 》公司动态
当前位置 : www.凯时首页 》新闻咨询讯 》公司动态 2019年4月14日,国务院总理签发第712号国务院令,公布《政府投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作为政府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条例》的颁布实施意义重大。自《条例》公布后,司法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等从《条例》制定的初衷、总体思路、积极意义以及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项目监管、对政府投资与ppp项目的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而且为进一步贯彻实施《条例》,国家发改委紧接着在5月6日专门发布了《关于做好<政府投资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796号),突显《条例》贯彻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主要运用南京卓远“投融资再平衡模型”[ 关于“投融资再平衡” 相关理念,详见南京卓远《投融资再平衡背景下区域开发综合解决思路》一文。],考察《条例》在整个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定位,并基于其定位分析《条例》颁布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政府与国资(平台)“公公合作”关系线规范的缺失问题。
一、《条例》在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定位
在“投融资再平衡模型”中,以“投融资主体”为视角观察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可以发现在整个投融资体制改革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法制化管理体系基本划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投融资主体各单线条的规范,包括政府投资与社会领域投资两类;二是投融资主体各关系线的规范,包括政府与国资(平台)间的“公公合作”、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公私合作”(如ppp、特许经营等)及国资(平台)与社会资本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三类。
在此框架下,《条例》在上述法制化管理体系中应如何定位?本文认为,因《条例》在第二条明确“本条例所称政府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其中,关于“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的理解,结合过往系列政策文件,以及《条例》第六条关于政府投资方式的规定,既然在政府投资方式上同时包含直接投资以及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间接投资方式,则此处“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即应理解为项目本身“包含全部或部分”使用预算安排资金的情况。而在采取资本金注入等间接投资方式时,实质上即主要涉及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或特许经营等模式,因此,《政府投资条例》实际上同时归属于政府投资领域的单线条法律规范和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关系线法律规范。
二、《条例》对过往政府投资领域法律规范的延续与发展
明确《条例》在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定位后,需进一步溯本求源,探究其法律条款内容与过往政府投资领域法律规范的关系。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即已明确提出要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等投资体制改革目标,至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出台,国家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上已取得新的突破。
在此期间,作为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发改投资[2005]1392号文)、中央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令2014年第7号、发改投资[2014]2129号文)、政府性资金对社会投资项目的支持(发改投资[2012]1580号文、发改投资〔2015〕823号文)、企业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令2014年第11号、国家发改委令2017年第2号、国家发改委令2018年第14号等)及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运行管理(国家发改委等十八部委令2017年第3号)等多个方面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政策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领域划分、监管方式等基础问题,但也带来“政府投资管理缺乏上位法,现有规章、规范性文件权威性不足、指导性不够、约束性不强的问题”。
《条例》即是在上述一系列法律规范基础上形成的,是对过往法律规范的延续与发展。一方面,从法律条款内容上来看,《条例》总体上并未颠覆过往认知,基本维持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原则,甚至在一些条款上是对过往法律政策的原文引用,如在第三条规定的政府投资资金投向及政府投资范围定期评估调整机制等,是对中发〔2016〕18号文的承继,但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一些调整,将中发〔2016〕18号文中“政府投资资金只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调整为“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删除了“原则上不支持经营性项目”的规定等;《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早在 2006年原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即发布《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建市(2006)6号),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一律不得以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的方式进行建设,不得将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作为招投标条件,此次《条例》再次重申此项规定,相信对于当前政府投资领域工程建设投融资模式乱象能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条例》也对过往政策规定进行了发展与统一,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政府投资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796号)文件中也指出,接下来要全面清理不符合《条例》的现行制度,且相关清理进度安排已提上日程。
三、《条例》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影响
基于上文分析《条例》兼顾了政府投资单线条法律规范和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关系线法律规范之定位,以及《条例》对过往政策的延续性与统一性,则对于政府方以资本金注入等方式参与的ppp项目或政府付费类、可行性缺口补助类ppp项目,即应同时适用《条例》的规定,但问题在于,对于政府方未参股的纯使用者付费类ppp项目,是否需适用《条例》的规定?因根据《条例》,政府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而企业投资,结合《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17年第2号)等相关政策,主要指企业在中国境内使用自己筹措资金以及使用自己筹措的资金并申请使用政府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等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因此,上述问题即进一步演化为:政府方未参股的纯使用者付费类ppp项目是否需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本文认为,这一类项目虽然不涉及政府方资本金注入,也不涉及后续的可行性缺口补助支出,但由于使用者付费类ppp项目也需按照ppp相关政策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且需单列政府承担风险带来的财政或有支出责任(当然“或有支出”本身并不代表必然发生,但为定性方便,在此不作细究),此项支出也需纳入财政预算。另一方面,ppp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既然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那么“政府参与”即为ppp项目的应有之意,无论是否使用预算资金,政府方均需对ppp项目进行监管、考核,因此,本文认为,在现有法律规范下各类型ppp项目都应依法适用《政府投资条例》,建议将ppp项目纳入《政府投资条例》管理范围,并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进行统一管理。
在此前提下,结合《条例》的规定,对于ppp项目,一方面,在投资决策上,项目单位应当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按照政府投资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报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批;另一方面,在项目建设上,应符合开工建设条件、工程变更程序要求、不得垫资施工要求、投资概算控制要求、建设工期限制、竣工验收要求以及项目后评价等工程建设系列要求。尤其《条例》在第五条提出“政府投资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国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以及第十八条明确“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等的规定,与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文件精神相一致,同时对于ppp项目即将大范围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来说,也应提前做好衔接工作。
但总体来说,《政府投资条例》是对过往政府投资领域法律规范的延续,在其颁布之前,ppp项目在实操中已按照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执行政府投资决策审批及项目工程建设规范,因此《政府投资条例》的施行在投资决策和项目建设管理方面能与ppp实操顺利接轨,并不会对ppp项目投资决策、建设实施造成较大影响。
四、《条例》对政府与国资(平台)“公公合作”关系线规范的缺失
基于国资(平台)区别于一般社会资本的“公”主体属性[ 关于国资(平台)定位分析等相关问题详见南京卓远《以“公公合作”的视角探讨abo模式的合理性、在政府投资精准补短板领域的运用及相关政策建议》一文。],则国资(平台)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投资行为应如何认定?本文认为,结合前述关于“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相关界定,国资(平台)在作为政府出资代表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资本金注入方式参与项目时,其投资行为应认定为政府投资行为;而基于市场化竞争、自筹资金参与项目时,其投资行为应认定为企业投资行为。在此前提下,建立在授权与契约基础上的“公公合作”模式能使国资(平台)的“企业投资行为”定性更加清晰,且按照《条例》,“政府投资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国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因此,对于实践中国资(平台)以代建模式承接的相关公益性项目,属于政府投资项目,应按照《条例》的规定安排预算资金,且不得由施工方垫资建设,这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另一方面也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由代建方筹资或施工方垫资的违规情形能有所遏制。《条例》在第三十三条及第三十四条也就“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未按照规定及时、足额办理政府投资资金拨付”以及“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等情形明确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从“投融资再平衡模型”中的“项目属性”这一要素考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大致分为公益性项目、准公益性项目及经营性项目三大类,政府投资领域与企业投资领域即在这三大类项目中进行划分。《条例》在第三条和第六条明确政府投资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对确需支持的经营性项目,主要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也可以适当采取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结合地方(如上海)国企分类改革理论,未来竞争类国企会更多投向社会领域投资项目范围,而公共服务类国企及功能类国企基于公益属性,会更多地投向政府投资领域项目范围。
综上,基于国资(平台)尤其是功能类国企主要以社会效益为首,兼顾经济效益,与一般社会资本相比具备更多的“公”主体属性,且上文所述国资(平台)在投资行为定性及投资项目范围上均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应将国资(平台)置于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独立主体进行规范,明确国资(平台)可经政府授权在特定项目领域进行投资经营,以形成完整的投融资领域政府、国资(平台)、社会资本各单线条规范及政府与国资(平台)“公公合作”(委托代建、abo模式等)、政府与社会资本“公私合作”(ppp、特许经营等)、国资(平台)与社会资本“混合所有制改革”各关系线规范的法制化管理体系。